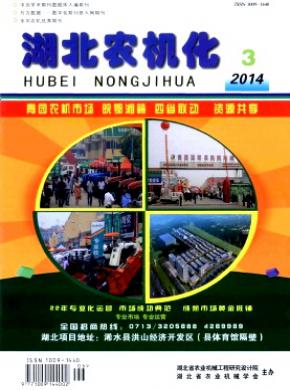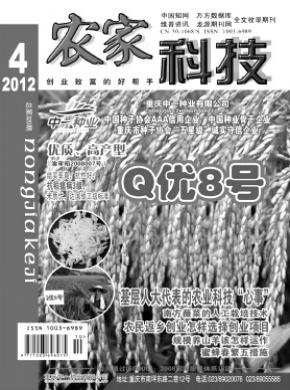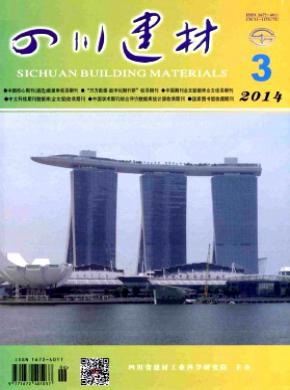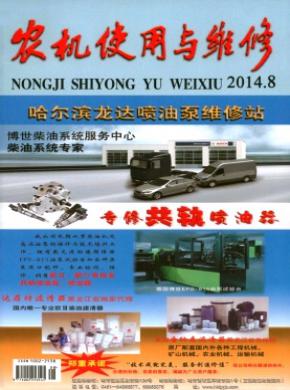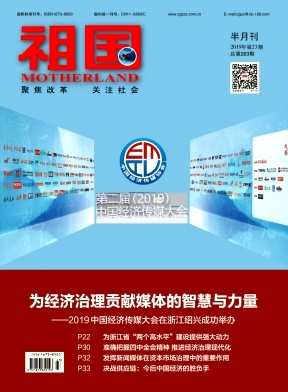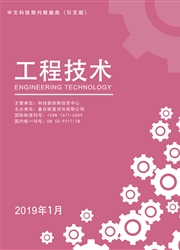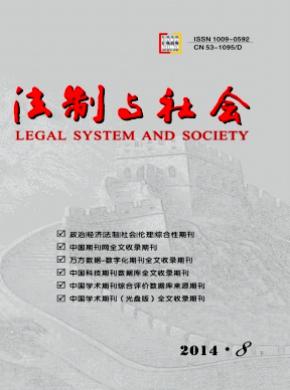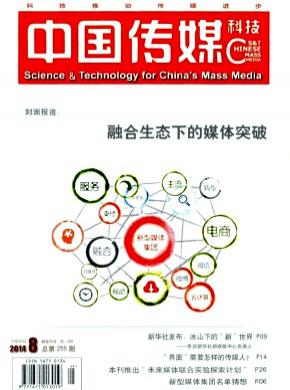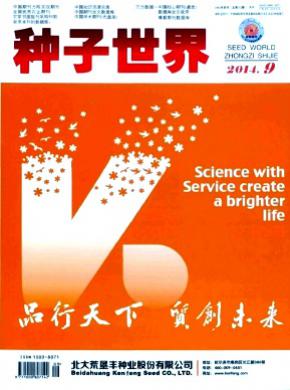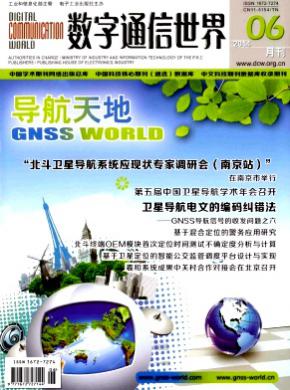新理论解释了古代地球是如何变得如此潮湿的
当地球刚形成时,它太热了,无法保留冰。这意味着我们星球上的所有水都必须来自外星水源。
对古代陆地岩石的研究表明,液态水早在太阳形成后 1 亿年就存在于地球上——在天体物理学的时间尺度上,几乎是“立即”存在的。
这些水现在已经超过 45 亿年的历史,通过地球的水循环不断更新。我的研究团队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水是如何首次到达地球的。
数十亿年酝酿的谜团
几十年来,天体物理学家一直在努力解决水是如何到达我们这个年轻星球的问题。最早的假设之一表明,地球的水是地球形成的直接副产品,在火山喷发期间通过岩浆释放,其中大部分排放的气体是水蒸气。
然而,在分析了地球的水成分并发现了冰冷的彗星,指向外星起源。
彗星是在太阳系遥远的地方形成的冰和岩石的混合物,有时会被喷射到太阳。当被太阳加热时,它们会产生引人注目的尘埃和气体尾巴,从地球上可以看到。小行星,位于小行星腰带之间火星和木星也被提议作为地球水的潜在祖先。
通过陨石(这些落到地球上的天体的小碎片)对彗星和小行星岩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通过分析D/H 比率– 重氢(氘)与标准氢的比例 – 科学家发现,地球的水更接近“碳质”小行星的水,这些小行星带有过去水的痕迹。这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这些小行星上。
最近的研究集中在确定可能将这些富含水的小行星运送到早期地球干燥表面的天体机制。已经出现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小行星体的“扰动”——小行星和柯伊伯带中大型冰冷的天体。
这些情景提出了引力相互作用,使这些物体移动,使它们飞向地球。这些事件需要一个复杂的“引力台球”过程,这表明太阳系的历史很动荡。
虽然很明显,行星的形成涉及重大的剧变和撞击,但地球的水输送有可能以更自然、不那么戏剧化的方式发生。
一个更简单的假设
我首先假设小行星从它们的形成茧(也称为原行星盘)中出现。这个茧是一个巨大的、充满氢的圆盘,里面充满了尘埃,行星和初始带就是在这里形成的。它包围了整个新生的行星系统。
一旦这个保护性茧消散——几百万年后——小行星就会变暖,导致它们的冰融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升华。在压力几乎为零的太空中,水在此过程后仍以蒸汽形式存在。
然后,一个水蒸气盘叠加在围绕太阳运行的小行星带上。随着冰的升华,圆盘中充满了蒸汽,由于复杂的动力学过程,蒸汽向内扩散到太阳。在此过程中,这个蒸汽盘与内行星相遇,将它们浸入一种“浴”中。
在某种程度上,圆盘为类地行星“浇水”:火星、地球、金星和汞.这种水捕获大多发生在太阳形成后的 20 到 3000 万年,在此期间,太阳的光度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增加了小行星的脱气速率。
一旦水被行星的引力捕获,就会发生许多过程。
然而,在地球上,保护机制确保水的总质量从捕获期结束到今天一直保持相对恒定。如果水上升到大气中太高,它会凝结成云,最终以雨的形式返回地表——这个过程被称为水循环。
地球上过去和现在的水量都有据可查。我们的模型从原始小行星带的冰脱气开始,成功地解释了形成海洋、河流和湖泊所需的水量,甚至是深埋在地幔中的水。
海洋中水的 D/H 比的精确测量也与我们的模型一致。此外,该模型还解释了过去在其他行星上甚至月亮.
你可能会想,我是怎么得出这个新理论的。它源于最近的观测,特别是使用 ALMA 进行的观测,ALMA 是一个由 60 多个天线组成的射电望远镜阵列,位于智利海拔 5 公里的高原上。
对具有类似于柯伊伯带的太阳系外系统的观测表明,这些带中的行星会升华一氧化碳 (CO)。对于离恒星较近的带,例如小行星带,一氧化碳太不稳定而不存在,而水更有可能被释放出来。
构建模型
正是从这些发现中,该理论的最初想法开始形成。此外,来自隼鸟 2 号和 OSIRIS-REx 任务的最新数据提供了关键证实,这些任务探索的小行星与可能有助于初始水蒸气盘形成的小行星相似。
这些任务,以及地面望远镜的长期观测,揭示了这些小行星上的大量水合矿物——这些矿物只能通过与水接触形成。这支持了这些小行星最初是冰的前提,尽管大多数小行星后来都失去了冰(像谷神星这样的较大天体除外)。
有了模型的基础,下一步是开发一个数值模拟来跟踪冰的脱气、水蒸气的扩散以及它最终被行星捕获。
在这些模拟过程中,很快就发现该模型可以解释地球的供水。对火星和其他类地行星过去水量的额外研究也证实了该模型对它们的适用性。一切都很合适,结果可以发表了!
作为研究人员,设计一个有效且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的模型是不够的。该理论必须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测试。虽然现在无法检测到“浇灌”类地行星的初始水蒸气盘,但我们可以查看具有年轻小行星带的太阳系外系统,看看是否存在这样的水蒸气盘。
根据我们的计算,这些圆盘虽然很微弱,但应该可以用 ALMA 检测到。我们的团队刚刚在 ALMA 上获得了时间来调查特定系统以寻找它们的证据。
我们可能正处于了解地球水起源的新时代的黎明。
昆汀·克拉尔, Astrophysicien à l'observatoire de Paris-PSL, CNRS, 索邦大学,Université Paris Cité